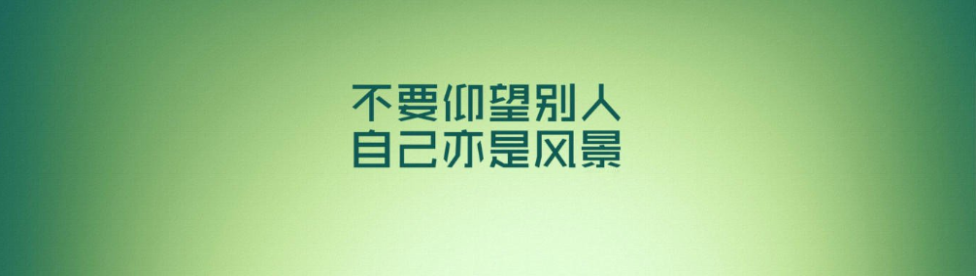电影《银翼杀手》:复制人是否算作人类?人性探讨
雷德利·斯科特的影片《银翼杀手》摒弃了传统好莱坞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武器”,而是以“赛博格”这个人物为中心,对人类和被复制人的关系进行了思考。这是一部以后人类为视角的电影,讲述的是“人”特有的记忆被植入到分身的大脑中,分身对自己的情感和经历产生了怀疑。
影片表现了复制者对爱情的追寻,以及人对复制者的主体认同。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出影片对人与人之间未来关系的思考。
人的主体性已经面临着消解,对人的重新肯定既是对二元性思维的一次反抗,又是一次对人的新生的机会。
在《银翼杀手》的后续电影里,那个拥有记忆的分身,在明知是假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守护那个假的父亲。人性之光可视为“赋予”人性之光和再生之光。复制者自己的情绪是真的,虽然这种情绪只是一种“符号”,但复制者的选择和思维却让他从记忆的“主人”变成了“客体”。
人类主体性的失落:认同与认同
像《银翼杀手》这样的科幻片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充满想象力的未来画面。在未来,人类会制造出一种机器,为人类服务,叫做克隆人。除了情感之外,复制体拥有人类所有的东西。因为没有记忆,克隆人无法确定自己的感觉,所以他们只能机械地执行自己的想法。
人们仍然把它当作“物”来看待,不把它当作“人”来看待,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还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有感情的人们。在那个时候,造物主赐予了一个名为“瑞秋”的复制体记忆,复制体根据这段记忆,对自己的行为有了一定的了解,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意识,这就是所谓的“自我意识”,将复制体与复制体区分开来。
这一刻,所有人都在想,这具分身到底是不是人类?当这一问题出现在人们的思维路径中,就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丧失,这些具有灵魂的类人机器人能否被归入“人”的范畴之中?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原始的人的主体性已经被边缘化了,人文主义的合理性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如果再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个有生命气息的克隆人,会不会觉得电影里的人和机器的爱情是假的,是假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思呢?归根结底,是人对自己主体性的失落。机械和人一样吗?长期以来,“人”这一概念都是围绕着人类亘古不变的躯体展开的,以躯体来肯定人的“主体性”。随着科技的进步,机器逐渐进入人体,人体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最初,人们试图用“人性”来证实人的独特性,但随着记忆的可复制化,这种“人性”的“他者化”也在逐步显现。人类可以接受克隆人的感情,克隆人也可以和人类产生共鸣。此时,我们需要用一种后人性的眼光去看“人”,而不是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单纯以人和事物之间的差异来看“人”。
非具体化的讯息,若要与人互动,与人共处,需要我们以与它(他)完全不同的态度,重新思考与它(他)的关系。人类的“迷失”:和“他者”产生共鸣在《银翼杀手》中,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了克隆人的情感流露。虽然复制人瑞秋的记忆已经被植入了,但她的经历和真实的感情却是建立在这种感情基础上的,她对戴克的爱是真实的,是一种自然的,没有任何目的的,是一种人性的流露。
这种同理心是“身—心”分离的直接后果。“人”在面对这种机械性“共情”时,产生了自身作为人类主体的“迷茫”。在科幻电影里,“机器之爱”并不仅限于科幻小说中。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机器媒介的爱和聊天机器的情感都是存在的,人面对类人的机器所产生的情感是真实和共情的。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人类对机械的信任,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人类对机械的恐惧。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情感是比较复杂的,在给予与付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交换概念,性格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情感的建立非常复杂。而机器自被创造出来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服务性的产品,是一种用来满足人的感情的工具。
它不需要你做什么,但却能在你需要的时候安慰你,还能跟你交流。人在复杂与简单之间进行抉择,在索取与给之间选择了相对简单的方式,并在这一过程中付出了真心,从而建立起了情感上的依赖。在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已经有了一种“共情”,但由于人性的差异,我们还是把这当成了“选择”。
机械的自醒:物体的“主体化”
在笛卡尔的身体二元论中,你和我的区别更多的是关于身体的“可分性与不可分性”、“次要性与本质性”的区别,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身体,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但随着胡塞尔现象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更多地关注人的精神和精神层面,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银翼杀手》里曾经有这么一段对话,克隆人的创造者说过:“除了情感,他们什么都模仿人。”我们开始认同他们,这种感觉很奇妙,他们没有情感,只有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你我都觉得理所当然。如果我们给他们一种过去的感觉,让他们产生一种情感上的依赖感和慰藉感,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控制他们。”
“是记忆赋予的。”
有了记忆,分身就有了真正的感情,他们可以通过记忆和现实世界的交流,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这就是分身有灵魂的原因。
这一被赋予灵性的复制人,面对人类“主体化”的“主体化偏差”,开始觉醒并实现自己的客体,从而向现代人提出更深层次的质问,更贴近心灵。借鉴后人性的视角,从“判断”、“成为”、“人权”这三个方面,对未来“人”进行了新的思考。
“成为人”:赋予回忆
从人的角度来看,克隆人始终是一种产品,人没有把克隆人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从“物品”的角度来看克隆人。
复制者所具有的感情,只不过是在其所能存活的时期内,对人类感情的认识所产生的一种模仿行为,他们对感情一无所知,只是模仿而已。
然而,在这出戏中,创造者为了让分身变得更有人情味,给分身灌输了记忆,让分身拥有了另一个人的“过去”,让分身产生了一种依赖,一种慰藉。但这里也产生了一种矛盾,为了区分克隆人与真实人物之间的区别,片方采用了瑞秋与戴克的对白。

存储器还可以用来对比不同机器的差别。镜头转到了一对机器之爱的情侣身上。另一方则是克隆女刺客和塞巴斯廷之间的爱情故事。这只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充满了利益与目的,影片中还用了一个特写来区分这种感觉的不同。
电影中,赛巴斯汀把女刺客当成爱人和朋友,但女刺客只是把他当成接近创造者的工具,因为她无法产生感情,只能通过表达感情来达到目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克隆人是无法理解感情的。
另一方面则是关于戴克与瑞秋之间的爱情故事。瑞秋表现出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爱,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那是一种在戴克最危险的时候,拯救了他的生命,同时,她也能感受到戴克失去了妻子的悲伤。这种从心底涌出的情绪,正是基于记忆而产生的。
“人的权利”:文化权利及其归属感
如果将复制者包括在内,复制者是否拥有与其文化记忆有关的权利?从实质上讲,这也是对复制者权利的一种认可。文化的连续性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基础,长久以来,人们只是把记忆本身视为一种单一的文本,而记忆中包含着情感和联系。
历史与现代的连接是人们哲学反思的源泉,我们对于文化内容的接受与再继承实际上是人类发展的接续,这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连接与沟通。自古以来,历史就充满了强烈的人文色彩,强烈的排他性使得机械与物体长期处于“客体”的位置。
它并没有被载入人的记忆,而是被当作一门专门技能来继承和发扬,为人类主体服务。但随著科技的进步,类人的趋向,使这些“物”更具“人性”。
在《银翼杀手》这部电影里,大反派都是在临死前爆发出人性的最后一丝光芒。分身罗伊不是杀了戴克,而是将他从濒死的边缘救了回来。在人类最辉煌的时刻,罗伊喃喃自语道:“这一切……时间……终将流逝……就像眼泪一样……消逝在雨水当中。”很显然,分身罗伊对自己的死亡,是非常平静的。
分身在临死前选择救下戴克,是不是也是为了摆脱自己即将死去的身份?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罗伊作为分身,有着极强的感情,他最后那句话中所蕴含的感情,足以打动任何一个有感情的人。
对于罗伊来说,“拯救”戴克不仅是一条回归之路,更是一条人性光辉最后的“爆发”。这些独一无二的克隆人所具有的人性光辉,也应当作为人类共同的记忆而被保存下来。属于人文内涵的文化,亦应寻找其对人类集体情感的延伸空间。
分身与真身之间的共同记忆已经很久很久了,强行将分身与真身区分开来,只是一种人道主义对“他者”界限的侵犯。
后人类主义对人和机器在“主体性”问题上的争斗和思索进行了阐释。也许未来的图景不再是单一的现实,不同的“主体性”存在,意味着虚拟和现实、异度和历史、情感和算法的不同互动,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有差异的未来。
虽然《银翼杀手》没有考虑到未来,但电影的风格(隐喻和悲观),却让人联想到了未来人类与机器人的共生。或许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很难分辨出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什么是虚幻,什么是虚幻。
凯瑟琳·海勒在她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写道:“后人类主义的环境为人类重新审视自己理所当然的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从而对人类文明进行去中心化的批判和反省。”
免责声明:本文为转载,非本网原创内容,不代表本网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
中影青年电影人计划项目启动首期10亿资金助力青年影人类型创作
搜狐娱乐讯昨日,“中影青年电影人计划”首期投资项目在海浪电影周正式启动,该计划由中影股份主导、全行业共同参与,旨在扶持新影人、 [详细] -
《万湖会议》定档 解密史无前例的人类清除计划
一场会议,15个人讨论,最终改变了1100万人的命运,让一个种族几近消亡,这样的事情你敢相信吗?然而,这就是不容争辩的残酷史实,也是电影 [详细] -
周作人的散文清淡又奔放 周作人文化底蕴浓厚,值得细品
感受文化,就像在花园里漫步一样,美轮美奂。 文化之美,令人陶醉周作人是鲁迅先生的亲弟弟,他的散文与小品的成就被公认为时代大家,备受 [详细] -
深刻走心的感悟句子 视野开阔,探索人生的奥秘短小精湛的说辞
宽容是一种美德,它可以让你的心境更加宽广。 容忍他人的同时,也要学会宽容自己。一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没有必要去跻身别人的生 [详细] -
世界唯一拥有不死细胞的黑人女性,细胞能无限繁殖
人类其实也是由一个个微小的细胞组成的,科学已经对此作出了证实,不过细胞的生命也不是无限的,当分裂繁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细胞也会衰老 [详细]